
在庄子看来,得道的方法就是“忘”和“虚”。“忘”即忘记外物及物我关系;“虚”即心灵进入虚无的境界。“忘”针对外在之物,“虚”针对内心中的障碍。内虚外忘,实即内外两忘,一旦虚、忘兼备,大道自成。
“忘”如同一个人经历一个“洗脑”的过程,把一切既有的东西从大脑深处洗干净;而“虚”的过程是人用心去领悟“道”,再把“道”“装”入自己的大脑中,与“道”融为一体。当然,“忘”与“虚”并无先后关系,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。
由于没有至上人格神的存在,庄子将虚拟化的“道”当成了人生的精神支柱。庄子哲学的中心是“道”,一切以“道”为根据。道是灯塔,是方向,也是归宿。庄子对“道”的描述,从本质上说是为其以人生论为核心的“人学”理论服务的,这突出地表现在庄子对于人生困境的追溯,对人的自由境界“逍遥”状态的刻画。
人生的苦难与逍遥在于“道”的得与失。道无处不在,得道便是与道合一,就是个体回归人的本质存在,就是融入大道之中。只有以道观物、以道观天下才能解除人生的烦恼与痛苦,最终达到自由逍遥的境界。因而,只有识道、悟道与得道才能真正地走向自由。
那么,是什么妨碍了人们识道、悟道与得道呢?
从外部原因看,人生在世,人们总是受到世俗中的各种欲望的驱使,导致了人的不自由状态。庄子认为,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意志受到了外在力量的制约,并且对此茫然不知,这就是人们对于人生本质认识上的“芒”。“一受其成形,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,其行尽如驰,而莫之能止,不亦悲乎!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,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,可不哀邪!人谓之不死,奚益!其形化,其心与之然,可不谓大哀乎?人之生也,固若是芒乎?其我独芒,而人亦有不芒者乎?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。
人一旦禀承形体的存在,生命就会存在于形体之中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它与外物互相较量摩擦,追逐奔驰而停不下来,这不是很可悲吗!终身劳苦忙碌,却看不到什么成功;困顿疲惫不堪,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,这不是很悲哀吗?这种人就算是不死,(活着)又有什么益处!他的形骸逐渐衰竭,心也跟着迟钝麻木,这还不算是大悲哀吗?人生在世,真是这样茫然吗?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如此茫然吗?而别人也有不茫然的吗?
从内部原因看,人类已有的文化思想内化在人心中,成为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,即所谓的“成心”。由“成心”产生的先入为主的“成见”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判断,限制了人们的行为,导致了人的不自由状态。“夫随其成心而师之,谁独且无师乎?奚必知代?而心自取者有之,愚者与有焉!未成乎心而有是非,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” 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。如果追随自己心中业已形成的成见,并把它当作老师,那么谁会没有老师呢?何必要明白事物变化的道理呢?从自己心中去找就有了,连愚人也一样有老师啊!如果说心中没有成见,却已有了是非观念,这就像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就已经到达了一样。
人不仅成为自己和外在世界的奴隶,而且一切都是从已有的“成见”出发,人的存在呈现出悲剧性景况。“梦饮酒者,旦而哭泣;梦哭泣者,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,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,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,而愚者自以为觉,窃窃然知之。君乎!牧乎!固哉。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。
一个人,晚上梦见饮酒作乐,早晨起来却悲伤哭泣;晚上梦见悲伤哭泣,早晨起来后却在欢快地打猎。人在梦中,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在梦中还在问着所做的梦吉凶如何,醒来以后方知自己是在做梦。必须要有大清醒,然后才知道是一场大梦,而愚昧的人则自以为清醒,好像自己什么都明白。整天君啊,臣啊,实在是浅陋极了!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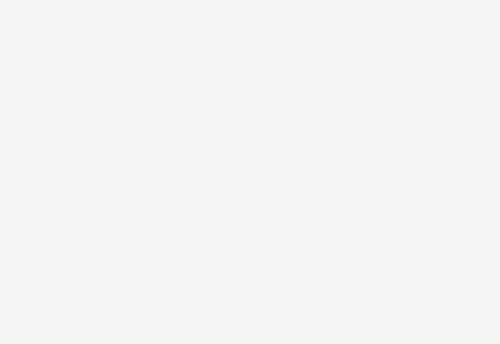
 返回栏目>>
返回栏目>>




用户评论Comm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