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旧时学茅山法的方式很有趣,听老一辈师傅说,学茅山法,都要半夜从师傅后墙的狗洞里面钻进去,然后师父会问:后面有没有人?徒弟答“无人”,则可以学习;若回答“有人”则不教。当然,经过这个仪式的法门,都是绝教。所谓“后面无人”,即是断绝子孙的意思。
词曰:竹林深处,几多名士隐流。古道旧观,青灯古佛,处处有真神。更有那,大隐隐朝市,似醉似醒,终日卧混沌。也见成名无数,败名无数,鱼虾相杂混。一曲未尽频添酒,明月映照处,诗向知己吟。
话说俺人,从小喜佛爱道,寻赜探幽,所见所闻,甚是不少。一晃年过而立,清风明月依旧,而昔日所遇见之高人隐士,或逝或隐,思之难免感而伤怀。唯恐中年事多,记忆忘却,也不忍往日所见之人,湮没于世,故将他们一一笔之于书,这也许是我为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了。
我最初接触法术,大概在十岁左右。那年我村来了一个篾匠师傅,帮家里补箩筐。农村的夏天,男人们洗澡,都在一个晒谷子的坪上。我和他各提了一桶水,准备洗澡。他突然说:“我站个马步,你肯定推不动我。”我说:“真的么?”他就扎了个马,我站他正面,想把他往后推,确实推不动。大概那时我认为自己还小,推不动很正常,所以当时也没在意。他临走的前一晚,在一张红纸上写了几句话,说这个口诀可以止血,我至今只记得其中一句是“日出东方一点红”,其他则完全不记得了。
李师,是我读书时候的哲学老师,省明清中哲学史委员之一。上课很风趣幽默,经常跟我们讲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经络理论。每天早上他都穿一身白色练功服,提着四个热水瓶来学校打开水,利用工人装水的时间,他会拔出一把长剑,在学校操场划起舞,他几乎是学校的一道风景线。我喜欢靠近他,问他练的是什么剑。他说是九天玄女剑,还告诉我他练剑的时候我必须站到他20米之外,我问为什么,他说怕伤着你。有一次他练完剑,对着一个人凭空划了一下,那人把衣服剥开,身上留了一道红痕,足见他这个剑气是有点威力的。
大概是一年的秋天吧,他坐在教室走廊乘凉。我笑着问他:“你能不能扛打。”他说:“可以。但是有个条件,你打我三拳,我得还你一拳。”我说:“我不能打老人。”他说:“没事。放心打。”我问他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诀窍,后来他说了,是寄打,茅山里面的功夫。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会茅山。
当然李师的内炼功夫也极高,他经常跟我说,人体的经络就像丝瓜络一样,他看的清清楚楚。在生时他经历过很多传奇的事,拜过很多师父。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是有一次在定中,有个人反复在他面前出现过三回。前两回他都没理她。最后一次出现他才问:“师尊是谁,是不是有什么要指点弟子?”那人回答:“我叫左安兰,住在石城......(某地),你可以来找我。”原来是阳师寻徒弟。第二天他便托人到该地打听,是不是有这个人,反馈的消息称,确实有此人。后来他专程去拜访那人,回来告诉我那人修的是数字功,两眼像猫一样放光,定身法和分身法都有成就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李师逝世。逝世前把他念的那几个数字告诉了我,由于我知道每个人的数字不同,他练的我未必能练,所以我没做笔记,后来就逐渐淡忘了。
李师是“文革”一代过来的,有阴影。他经常对我说,“文革”时期,害的你最惨的都是你的朋友,所以他一辈子都不交朋友。甚至他也不教徒弟,我估计也仅仅是他的学生而已吧。遗有《茅山雷坛道法》一册。开悟时有一偈子:“师也空,徒也空,空悟悟空,无德无功。”
余授业恩师上悟下净和尚,俗名姓陈讳金彪,民国时期著名江湖客肖红山嫡传弟子,茅山绝教,“文革”后隐于佛门。我向老一辈的人打听过,肖红山确有其人,走江湖很出名。我师常给我讲,他老人家八十多岁还能表演空中飞云(一种腾空法术)。
陈师在宁都地区神迹颇多。李师跟我说过,他小时候曾看过陈师的表演,八张桌子叠在一起,从下面往上翻,翻到顶后又翻下来。轻身功夫卓绝。以至于李师六十多岁在我的引荐下见到陈师还想拜师学功。
宁都长胜盘龙窝留有陈师的一则传奇。陈师有个契女嫁到此处。大婚那天,下大雨,只见这老和尚拄着拐杖从雨中走来,众人认为这下和尚要变成水和尚了,结果到了屋里一看,老和尚身上一点雨水都没沾着,都惊呆了。后来我专门为此事请教过老和尚,他说是一种避雨术,使用这种法术也可以让身边的人不淋雨。
我跟陈师在一起时,他已近百岁,他经常演示脱身法(遁术的一种),以验证自己的法力尚未衰退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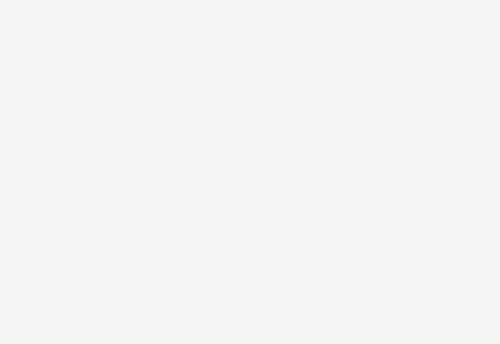
 返回栏目>>
返回栏目>>




用户评论Comment